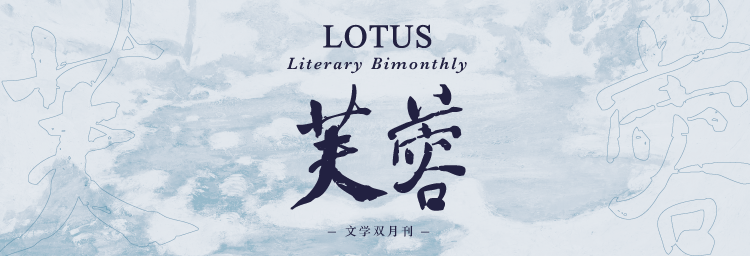

黑箱子 (中篇小說)
文/許玲
1
那天凌晨醒來,我忽然認識到本身好久沒有做夢了。我曾經習氣一邊吃著早餐,一邊從黑甜鄉里撈出一個比擬清楚的片斷,不經品味,便將它們吐在飯桌上。張蘭端詳著我,似乎我是一個忽然冒出來的生疏人。她說,這不成能,你不是沒做夢,你只是不記得了。昨天打德律風要你帶瓶醬油回來,你那時正在超市里面呢,你都包養忘卻了。她不無憂慮地皺起眉,傳聞老年聰慧有家族遺傳,你爺爺就是這病,你得警惕點。我憤怒于她老是果斷地給我安上各類疾病稱號,似乎她是一個隨身攜帶了超聲機的大夫,清楚地照出我的脂肪肝、腦血管硬化、頸包養網椎病,還有心律變態。我們爭持了幾句之后,我就開車出了門。
截至此刻,我最后一個清楚的夢是關于祖母的。夢里我很甦醒地了解,她曾經逝世往多年。當一個女人流著淚的臉呈現在我眼前時,我差點認為她是一個生疏的白叟,由於我從未見過她流淚的樣子容貌。當我看清她身上藕荷色綴暗花的旗袍,玄色帶金絲的盤扣一向牢牢扣住下巴,眼淚也無法沉沒她的冷淡臉色之時,我頓時就斷定了——這恰是我的祖母。一些年前,她和祖父一路并排掛在堂屋的神龕上方,被歲月風化的眉眼,含混地附在發黃的照片上。可是,祖母一向堅持著我印象中的倨傲神色,并未由於褪色而掉往半分,這讓她與其他做了祖母的女人差別開來。而祖父,和他人家堂前被高高掛著的慈眉善目標老頭差未幾。這沒有什么,人假如有幸活到必定歲數,就會漸漸掉往本身的特征。希奇的是,無論我從哪個標的目的凝視著祖父,他都能超出我的存在,盯著遠方。我們家創新過一次屋子,簡直是舊址重建,屋子是他們留上去的,骨骼變形,內臟腐敗,不了解哪天就會中風猝倒包養。我將祖父取上去,放在我的眼皮底下,我和他面臨面臨峙很久。阿誰悶驢般誠實、人皆可欺的老頭逝世了才開端背叛——我偏不看你們。我將他們隨手放在一張漆面斑駁的八仙桌上。比及新家建成的時辰,我才發明“他們”不見了。張蘭將“他們”葬于一片早該回西的瓦礫朽木之中。
在夢中,祖母和我置身一間濕潤暗中的屋子里,無窗,周圍的墻壁有著粗拙堅固的質感,好像一個被水泥糊起來的四方盒子。屋中心有一張被舉高的木板,她緘口不言,徑直朝它走曩昔,躺了包養上往,竟是一張床。我在齊膝的淤泥中以一種艱巨跋涉的姿勢走近,床板上厚厚一層稀泥,她的身材一會兒陷了出來,只顯露一個腦殼。她就用這腦殼看著我,卻不措辭,像一個伐罪者。我頗覺氣憤,高聲質問,你怎么睡在這處所呢?這是誰弄的?
我醒過去之后,猜不出這個夢的寄義。由於祖母簡直不走進我的夢里,一如她生前性格生冷,不喜人接近。並且,如許的工作在她在世的時辰是完整不成能產生的。她的房間,包含她全部人都明哲保身。我回想起全部黑甜鄉,她都沒有對我說一句話。我想,這卻是可以懂得的,由於我早已記不起她的聲響,她那時可以成天不吐出一個字。我將這個夢告知了張蘭,她卻以為這個夢還有寄意。更年期開端之后,她將一切超越正凡人生包養網軌跡的工作都說明為命。她說,除了命,怎么往說明這些希奇的工作,不是你,不是我,為什么是他?早一秒,晚一秒包養,這工作就不會來。她既然來了,就必定有要告知的工作。我不認為然地說,我和她又不熟。要來托夢也應當是老頭子,怎么是她呢?我卻是常常夢見祖父,在何處的世界也種了幾十畝地,穿了件灰色的褂兒,像只鴕鳥一樣躬身在稻田里。如許的場景呈現過好幾回,我感到阿誰世界或許與這邊無異,只是一個地上,一個地下。納福的還在何處納福,當長工的照舊做了長工。
張蘭的筷子停在半空,一副豁然開朗的樣子,我了解這個夢的寄意了。她衝動地說,奶奶的墳離水近,旁邊就是一條河。我“嗯”了一聲,她持續說,你不感到你夢中的阿誰屋子就是一具棺材嗎?奶奶住的處所地勢又低,一漲水,就能淹到她的屋子,里面確定就是泥沙啊。我驚惶地看著她,似乎名頓開,那四方無窗的屋子不是棺材,又是什么?張蘭獲得我的承認,情感愈加低落自負,她說,祖先托夢,屋子近水,后人晦氣。難怪,你這平生運勢平平,才五十五歲,就成天叫著脖子痛、頭痛。
我前提反射般地辯駁道,我固然只是師范黌舍出來的中專生,可那是什么年月啊,我爺爺昔時可是放了一場片子,幾個村的人都到了曬谷坪,像過節般熱烈了年夜半晚的。可是,我的氣勢很快便低了下往,張蘭說的不無事理。我這年夜半生像釘子一樣扎在了村落小學。近年,村落黌舍合并,一個鎮上只留有一個中間黌舍。我終于被拔出來,從頭換了一個處所,由班主任提成了教誨主任。可是幾十年曩昔,釘頭曾經銹跡斑斑,早無銳勁,只等退休。我沒有兒子,只要一個女兒。誕生時在她媽肚子里多待了兩個禮拜,干什么比都他人慢一拍。唸書下面像嗑瓜子般磕磕碰碰,最后讀了市里的幼專,在幼兒園成了一個孩子王,天天嗲著聲響和孩子們措辭,男伴侶都沒有混到一個。對了,我還有一個妹妹潘知遠,傳聞她一小我在japan(日本)混得風生水起,到此刻都是孤苦伶仃一個。我與張蘭磋商,那我們怎么解?張蘭對我翻了一下眼睛包養,不是說那片墳地要遷出嗎?
我先開車往了一趟后山,比來雨水充分,荒草瘋長,將祖怙恃的墳頭掩飾得像兩個發了霉的饅頭。實在,這塊崛起的處所連山包都談不上,就像一個被蚊包養子咬了幾個年夜包的胳膊,有了幾處升沉而已。小河里的水曾經溢出來,離他們的墳頭不外幾米遠,腿伸長點,直接可以在里面洗腳。這條河往前兩百米,是新建的一段高速公路。站在此處,耳邊滿是咆哮而過的car 聲響,驅趕了蕭瑟之感,也占領了這里本應擁有的靜穆。過了高速帶,對面是一片新辟出的別墅區,房價讓僅有一路一河之隔的鄉間人咋舌。城市就是一個不竭收縮的瘦子,我們村曾經從鄉間釀成了城郊,很快就會釀成城市的一個末梢。此刻這條胳膊上,枕著我們村里的祖先,依照時光次序從東到西不竭舒展,密密匝匝地組成了另一個世界的潘家村。他們的屋子好像被風吹起來的雞皮疙瘩,風把草吹得一浪一浪低下腰往,它們就一座一座高高下低地顯顯露來。我眼前緊臨的兩座,似兩個頭挨頭遠望遠方的腦殼,它們被我制造得這般親切。我裴母蹙眉,總覺得兒子今天有些奇怪,因為以前,只要是她不同意的事情,兒子都會聽她的,不會違背她的意願,可現在呢?選擇阿誰處所,是由於祖父一輩子除了干活之外,暮年甦醒的那幾年,常拿著釣竿在此垂釣。祖母比祖父早走三年,但那包養時我就曾經提早啟動了如許的心思。祖母已經對妹妹潘知遠反斷交代,她和祖父生分歧床,逝世分歧穴。潘知遠是和祖母關系比來的人,可是,她遠在japan(日本),在這個家早就掉往了話語權。我果斷地選擇讓他們在一路,還有一個主要的緣由。我那不幸的被我祖母奴役了平生的祖父就不應讓她事事如意。不外,他們并未同棺同穴。他們更像鄰人,就像他們生前,以堂屋為界,各自占據一間房。逐日包養網從各自的房間里走出來,像分歧世界,也像分歧時空的兩小我。
我在離祖母幾步遠的處所點上了一根煙,我想象著她那肥大,全部線條繃得生硬的臉,索性離她更近一點。我還在地上爬的時辰,她坐在那把專屬的圓形玄色藤條椅上,一只漫步的雞和我差未幾同時離開她的腳邊。雞在我身邊拉了一泡屎,她沒有抱起我,而是將本身和那張椅子挪得離我們遠一正要離開,好遠,還要半年才能走?”些,似乎我和那只隨地拉屎的雞才是同類。如許的場景,我當然不記得了。這是村里那些白叟活著時講的,用他們的話說,盤古開六合以來,沒有女人如許當母親和祖母的。他們每次見到我,城市說,阿誰天天摸雞屎的孩子,也長年夜成人了。
此刻,哪怕祖母再討厭我,氣得從地里飛起來,也不成能像搬把椅子般將墳挪走了。關于遷墳一事,我并不焦急。實在早在幾年前,村里就曾經有了風聲,這片墳地是必需遷走的。比來似乎連每日天期都定了上去,一個新處所,必定會往舊迎新,要有新穎的血液活動和滋養才幹活上去。沒想到,祖母究竟沉不住氣,來找我了。
我駕著車隨著導航儀里的聲響,朝一個叫野馬鎮的處所開往。高速公路上的唆使牌一塊接一塊從我頭頂下面飛曩昔,我離它越來越近。阿誰鎮境內有一座山,叫鳳山。它明白地橫列在衛星輿圖上。從高速高低來,進進省道,接著是鄉道、村道。沒多久,就見到一條河,好像門衛般蓋住我這個外來者,我聽獲得河水流淌不息的聲響,卻不知它奔往何處。視野遠處是綿延的青山樊籬,近處是一小塊長勢旺盛的稻田。好像一副宏大的骨架之上,托出的一張清秀的臉龐。
這個處所是我一向想來的處所。它算不上路途遠遠,從出門到此刻,僅僅花失落了四個半小時。我認可,假如不是張蘭的正告,我只會在更遠些的將來才幹離開,或許,再也不來,就像有數樁想完成,卻終極沒有完成的工作一樣。人老是到必定年紀才想到往做某一件事。就像我的祖父,他將本身快丟完的時辰,才想到要回家。這并非遠不成及的間隔,是他平生再也沒法回頭的路。
2
當我將車停在河濱,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從升沉的稻田中穿曩昔,走向那座叫作鳳山的山。我祖父最后三年的抽像,也從我的腦海里走出來,到達了他在我腦海中最清楚的狀況。
先進場的是他一對氣勢的濃黑眉毛。進進老年,它們像蝙蝠一樣飛上了他的眉梢。他年青些的時辰,它們長在他臉上,共包養網同他早已低眉順眼的神色,就有了一種奇怪幽默的後果,像是一個慣于討人歡樂的小丑居心將眉毛貼反了。到了性命的最后階段,它們又與他的神色同一協調起來。我祖父在記憶開端凌亂和不竭喪失的那些日子里,又漸漸從統一具身材里長出了另一小我。好比,他一向溫柔的性質忽然布滿了倒刺,性格急躁,見人就罵,有時沖到路上對著空蕩蕩的途徑也要罵上幾句。村里不了解他內情的年青母親恐嚇孩子,再不聽話,把你送到潘爹家往。最后那一年,他的話語變得生澀難明,高亢尖利,和我們潘家村一望無際的聲調已是判然不同。
從不愛出門的他,某一天提著一個布袋單獨出了門。從此包養以后,他就天天出門。每次道路基礎固定,出了村口,一路向東北而往。由於我和張蘭逐日尋覓的消息,大師都了解了他,他在鄉下從未擁有過這般著名度。年夜部門時辰出了村口,他城市被熟人發明,像牽頭走掉的牛般拉回來。最遠的一次,等我們發明的時辰,他曾經爬過了離家七八里地的某個鐵路橋,站在鐵軌上,像一個游魂。一列載貨的火車在我們的視野下,恰好顛末他身邊,他全部人似乎在高空翱翔。有一次,他消散了。簡直一個村,包含派出所都出動了。我們最后將目的鎖在了一個遍包養布野山茶籽的樹林,那里有近百年將近成精的山茶樹,也有沉沒年夜腿的灌木。我們確切在那片山林里找到了他,他一動不動地躺在樹下的衰草叢里,如一條曾經回隱于年夜地的秋蟲,我上前將他輕飄飄的身材抱起來,在初冬的山里待了三天,他居然還在世。他早曾經不熟悉我了,卻抱緊我的脖子,包養網像個孩子般干嚎,我要回家,回野馬,回鳳山!
當我走在路上,碰著了從何處過去的第一小我,他騎著一輛摩托車迎面而來。我高聲喊道,老鄉,請問后面那座山是鳳山嗎?他的車停在離我包養十多米的處所,我不得不失落頭走曩昔。他對生疏的面貌有著天然熟絡的自在,問道,第一次來?我說,是的。他說,此刻鳳山是叢林防火特護期,不準游客出來了。前段時光,有人在那里搞燒烤,差點起了年夜火。我給他遞上包養一根煙,他取下頭盔接了曩昔,那是一張不算年青的臉,看上往比我還長上幾歲。他從襯衣口袋里取出一張手刺給我,我接了曩昔。他姓張,運營著一家農家樂,卡片上寫著垂釣、燒烤一條龍。我說,那下次來這里玩就便利了。我順勢向他探聽一個叫潘青山的白叟。他確認了一遍,確定地說,沒有這小我。我說,你傳聞過這個名字嗎?他說,假如是出往打工了的年青人,那我認不全。我說,不是年青人,是白叟。他說,住在這兒的白叟,我都熟悉。一支煙抽完,他也沒有想起潘青山是什么人。他幾腳把摩托車踩得冒了煙,對我說,我們鳳山一帶沒有姓潘的。
實在,這小我一啟齒包養網,我就斷定了這是祖父想回來的處所。哪怕他把我看成外埠人,包養咬著一口走調的通俗話。當摩托車的聲響消散在遠處,我忽然認識到,本身犯了個過錯。祖母姓潘,祖父也姓潘,這應當不是夫妻擁有異樣姓氏的偶合,而是由於包養祖父流落在外包養,丟失落一個姓氏是無所謂的工作。這個世上,除了我之外,不會再有人關懷祖父究竟從何而來。那些了解祖父是良多年的一個秋天離開潘家村的白叟,都已依照次序往了地下。他們說,祖父背著一個灰色討米袋呈現在村里的時辰,全身的傷口都在流膿。阿誰年月,他們對于呈現在村里的老花子見責不怪。這個老花子應當是被餓狗咬了,不外阿誰年月,窮得連狗都少見,那應當是被人打了。村里的外姓,一個姓張的老頭說,他屋里那時還給了祖父一個裹著紅薯的飯團。最后,祖父沒有再走出村莊,暈倒在潘聘才家的牛棚里,潘家的牛棚里有兩端牛。潘聘才是我祖母的父親,潘家村最有錢的年夜戶。那時啊,張老頭每次說起這事,城市用手指著村西邊那片山茶林的標的目的,在空中畫一個年夜圈,再落回東邊那片田里,他說,一年夜半個潘家村的地都是潘聘才家的。我問,后來呢?他咧著牙齒失落無暇空的嘴笑,不再措辭。后來,一張床,一碗稀飯救了祖父的命。祖父做了潘家的長工,又過了幾年,和祖母潘學珍結了婚,做了潘家的第三頭牛。
對于此刻的潘家村,祖父上門女婿的成分并不是一件值得說道的事了。潘家村這些年接收了良多外來的人,姓氏早就變得八門五花。有從外埠投靠親戚留下的,有由於遭受洪災,家園釀成了蓄洪區分流到此的,還有兩戶是外省來的三峽移平易近。只是在更早些的年份,碰上過年、中秋如許嚴重的節日,一個姓氏,沾親帶故且同在一個祠堂的本家親戚常集聚在包養網一路。每當如許的時辰,常會由於祖母出格的表示,祖父的成分就像一個石頭袒露在斷流的河床上,不得不惹起人的留意。
祖母穿戴綴著盤扣的深藍色棉襖,頭發盤成一個年夜餅,用一個玄色網狀的罩子套住,一根雜毛也不會探出來。我已經在一個被尿憋醒的凌晨,見到過她站在門邊的晨光里梳頭發的樣子,頭發好像瀑布一樣垂在腰際。她年青的時辰應當是一個都雅的人。都說潘知遠長得很像她,而潘知遠就是一個水靈的佳麗。祖母老了后,好像供桌上那些鮮亮的生果一樣,固然掉往了水分包養,可是她的做派卻愈加令人不敢褻瀆。她那種做派,和村里那些帶著孫輩的老婦人判然不同,她給本身搭了一個高架,將本身置于神壇,哪怕被那些孩子說成是修煉了一千年的老蛇妖也絕不在意。欠好聽的話,她聽得太多,歷來不把這當回事。從我懂事時起,她便作為全桌獨一的女人,坐在主位上,背部挺得筆挺,神志嚴厲,在全族年高德劭的漢子中穩如泰山。她不常措辭,漢子們給她敬酒,從飯局開端到停止,她手中那小盅酒才喝完。女人們看著她笑,對她的挺拔獨行都顯示出一種敬而遠之的包涵。我一度認為是由於祖母位置的不同凡響。有一年炎天,我們村的人在公路上碰到一個穿戴棉襖的流落漢,他蓬亂著頭發,嘴中念念有詞在我們的村路下游晃了幾天。我們撿起石頭朝他身上扔往,包養網大師一邊笑一邊禁“那這不是離婚,而是對婚姻的懺悔!”止我們。他們同阿誰流落漢措辭,問詢他從哪兒來,他的答非所問和驚駭臉色引來一陣又一陣年夜笑,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了一種熟習的工具,恰是他們已經施舍給祖母的笑臉。在飯局開端前,他們城市居心站起來,東張西看尋覓祖父的身影,嘴中叫著,潘爹呢?把他也請過去一路坐啊!
祖父在如許的場所,從未上過主桌。他將本身混于孩子們那一桌。有時,連桌都不上,幫著廚房里幹事,埋著頭和女人們在廚房就把飯吃了。他炎天穿戴一件灰色的襯衣,冬天穿戴套著灰色罩衣的棉襖,他對灰色的偏心,一向連續到逝世。灰色成了他的另一層皮膚,將他暗藏起來。縱是如許,他和祖母之間做派、位置的宏大差別,是必定會被人講起的。
我由此了解祖母是讀過書的女人,傳聞讀的書,比我和姐姐都要多。可是,我以為那只不外是夸張,由於在阿誰年月的鄉間,識字的女人都是百里挑一。一只雞,在那么多人的嘴中會被傳播成一只鳳凰。我已經問過祖父這個題包養網目。他可貴地顯出一種驕傲,她學問年夜,什么字都熟悉,還能教潘知遠寫文章。我又問祖父,到哪里讀的書呢?他搖頭說,那我不了解。
祖父確切不了解。他面臨祖母時,就像一個餓極的流落漢,不論後面是什么菜,從不停止回味,只會選擇一股腦吞下往。在我進進少年,我一度猜忌包養網父親是不是他們的孩子,他們完整不像無機會能制造出一個性命的樣子。我已經和潘知遠會商過此事,可是,她對此全無愛好,沒有答覆我,只是斜瞟了我一眼,用鄙棄的眼神告知我,這是件很是無聊的工作。和那些站在路上,對著我們家像地痞一樣吹口哨的少年一樣令人討厭。我了解,她必定了解祖母的良多工作。要否則,祖母靠什么往教導她,讓她簡直成了從祖母身上臨蓐出來的別的一個祖母。她熱愛玄色的裙子和白色的娃娃襯衣領,就算在炎天,襯衣領也會扣得一絲不茍,她從不穿涼鞋,穿戴厚厚的齊膝的白色襪子。背部挺得筆挺,像有人不時在反扣著她的雙肩,不讓脖子前傾。她吃飯,喝湯歷來不會收回一點聲響,穿戴冬日拖鞋的時辰,像只貓走路一樣,不會弄出踢踏的聲響。她一點不像從我們屋子里走出來的女孩子。村里人說潘冬子像她的祖母,而我則像那悶棍子打不出半個屁的祖父。沒有人說,我們像本身的怙恃。由於,他們就是我們的怙恃。
我想著曩昔,鳳山已到腳下。兩座高峻緊臨的山嶽像母雞的兩個肥碩的同黨,將全部山村包抄在本身懷抱里,腳下如小雞般蜂擁著一圈人家。和此刻年夜大都鄉村一樣,除了幾聲雞啼狗吠,站在屋前獵奇地端詳著我的,多是些上了年事的人。還有幾個穿戴短褲,赤著腳,既靦腆又無邪的小孩,見到生人,笑笑后像吃驚的小鹿普通躲進屋里。這片老了的地盤發展出了一年夜片重生的工具。幾幢帶著尖頂和羅馬柱,卻又袒露著紅磚外墻的村落別墅,兩層寶蓋頭,有著廣大堂屋年夜門的樓房,一色籬笆笆圍起來的菜園,它們一路籠罩了曩昔一切的陳跡,包含祖父從這里走出往的足跡,我用了一個下戰書的時光,簡直問遍了山腳下一切人家。無論是潘青山、胡青山、張青山,都沒有人能從腦海里挖出一個與青山有關的人。
入夜的時辰,我按有名片地址往了阿誰農家樂。張哥正招待一個來搞聚首的單元,忙得不亦樂乎。好幾小我正圍著煙熏火燎的燒烤架妙語橫生,架上放著一只曾經萎縮的全羊。另一邊,為篝火晚會預備的木頭已搭建得像個浮圖。他一見到我便關懷地問,人找到了沒?我搖頭說沒有。他一邊給只剩下輪廓的羊身撒下一年夜把辣椒粉,一邊問,上午和你說了半天,你都沒有告知我,他多年夜年事了呀?我笑了笑說,假如在世,應當一百零幾歲了。他張年夜了嘴,問道,是你什么人啊?這時,站在他旁邊的女人打失落自家孩子伸向羊腿的包養手,高聲喝道,燙不逝世你!
篝火點起來的時辰,農莊里熱烈不凡。舞臺的聲響,像一群嘶吼的野馬,向對面的山頭奔往,讓全部山都有了回響。我坐在一旁緘口不言。從我步進天命之年之后,孤單似乎就成了我的親兄弟。我沒有兄弟,這時我想到了應當加倍孤單的潘知遠——我們幾多年未見了呀。
我給她發微信:我夢見祖母了。我在屏幕上耐煩地敲下了工作的始末,我告知她,本身曾經離開了祖父的家鄉,野馬鎮的鳳山腳下。潘知遠的信息很快回了過去,速率之快讓包養我很是不測。我習氣的是,我早晨發曩昔的信息,有時要比及第二天,甚至第三天賦能收到回應版主,內在的事務簡練,好像電報一樣包養網。她回道:等疫情停止,我想回家一趟。我才做了手術,已出院。
潘知遠用了家這個字,讓這些年冰凍的感情剎包養時凍結,我的眼眶被它沖擊得決堤。疫情還沒有開端時,女兒潘月和張蘭往過一趟japan(日本),臨走前,我在微信上告知了一聲潘知遠。她沒有表示過多的熱忱,只是沉著地回應版主了一句,好的。潘月回來后一臉高興,姑姑對她們很親切,最基礎不像我說的那樣冷血。姑姑擁有一個電子公司,她們往觀賞她的公司,碰著的每個員工城市對她們鞠躬問好。潘知遠替她們買了一年夜堆工具,此中幾年夜包養盒醫治灰指包養網甲的藥水、用于跌打毀傷頸椎痛的久光膏藥貼是給我的。潘月那日站在鏡子前問我,我長得像姑姑嗎?我實在早就發明,她的臉型和眉眼都和潘知遠神似,可是那種神韻卻完整分歧。我說,不像。潘月嘟著嘴,她都說像呢,她還激勵我往japan(日本)留學呢。
我想,歲月、疾病都是可以轉變一小我的。潘知遠躺在手術臺上時,她一小我簽下手術知情書時,一小我寧靜地坐在空蕩蕩的屋子里時,必定和我一樣,等閒地就回到了曩昔。我的雙眼霧氣騰騰的,寫道:潘冬子,一小我在裡面,要照料好本身。假如你回來,我們的家永遠接待你。假如不愿意走了,就留在潘家村。
(本文節選自2023年第3期《芙蓉》中篇小說《黑箱子》)

許玲,1979年12月誕生于湖南岳陽,現居常德。中國作協會員。作品散見《中國作家》《小說月報·原創版》《湘江文藝》《芳草》《清明》《湖南文學》等刊,有小說被《小說月報》《小說選刊》轉錄發載,曾獲《湘江文藝》雙年優良短篇小說獎,出書長篇都會小說《向前三十圈包養網》《南回北回》等。